七岁开始陷入对死亡的恐惧,我怎样实现了生命的重建。
七岁开始陷入对死亡的恐惧,我怎样实现了生命的重建。
长风|作者本文共计4400字,预计阅读时间10分钟。
第四期“乐平讲堂”正在报名中,文末查看详情
提要:我期待有一天,也相信有这么一天:我们可以接纳我们的“障碍”,不必给自己贴一个很重的“病人”标签;社会也可以接纳我们的“障碍”,不再视我们为“不正常人”而排除在很多社会活动之外;人与人之间是包容性的平等,我们的社群与社会大众不再有一个所谓的界线。
开始只是求助、自救,后来成了生命中的热爱
“我活到今天是个偶然,也是一种必然。”
这句话可能是我说的最“托大”的一句话,似是在突出自己的不易与励志。但我心里确实是这么想的。
从7岁开始陷入对死亡的恐惧,每隔几晚发作时浑身就会瑟瑟发抖,陷入恐慌、失眠(用当前的医学评判或许可称之为恐惧症、恐惧障碍),小学还好,进入中学时代恐惧、失眠开始泛化,衍生出泛化的焦虑以及哮喘、骨痛等躯体症状(当前医学称之为焦虑症?躯体化障碍?)。
进入高中,各项“指标”进一步加重,还出现强迫性思维和行为,直至高考前夕的崩溃(当前医学称之为强迫症?崩溃也就是抑郁症彻底爆发?),我终于走上了“同精神疾患抗争”的道路。

一路走来便到了今年,近30年。
这近30年里,我在连续的7年多时间内有自杀念头和行为,大多数时候是我在最后关头放弃,也有些时候是被父母、朋友、同事、警察救下。现在回忆起来,确实有种“英雄回首”之感。但在当年漫长的岁月中,没有语言可以描述那种感觉。
即便我在彻底放弃自杀念头之后的大概5年里,因为道路的艰辛,我还时常后悔当初为什么没有“走成”。直至遇到我诚挚为“灵魂伴侣”的妻子,我才开始对生活真正燃起希望,我时常对小崇拜我的妻子说:“我活到今天,真的是个偶然,感恩有你。”
有不少知道长风的朋友,除了抑郁症,公益、跑步以及胖子便是我的“标签”。
胖子,就是我的妻子,除了我自身的不屈和努力,她是对我心灵疗愈最为重要的因素。而跑步,也是我认识妻子之后第三年开始的,每天坚持奔跑10公里,至今已完成了17次马拉松,虽然并不像外界认为的“我通过跑步”而“治愈”,但跑步本身确实为我提供了巨大能量。
胖子时常鼓励我:“老公,你那么努力,能走出这黑暗也是必然。”每每听到类似鼓励,我都会回馈胖子:“若不是同伴支持,若不是曾经我自称的公益,我不知道能不能遇见你,能不能改变生活的方向。”

记得很清楚,那是2003年的春天,我在网上搜索“如何自杀”时,发现了“阳光工程心理互助论坛”(中国最早的抑郁症互助组织,也是中国“民间抗郁史”的源头),在里面认识很多跟我类似的“病友”、获得温暖的同时,我也走上了后来曾称之为“公益”的路,算到今年,我参与推动“同伴支持”已经15年:从一开始的求助、自救,到如今成了我生命中热爱与“要做的事情”。
太多歧路,唯有“同伴支持”才是我的方向
说来惭愧,每每讲述自己在“公益”“同伴支持”领域坚守15年时,我常会解释一番:早期的很多年,我只是自救、助人自助,直至2012年我遇到尚善基金会(中国大陆第一家关注精神健康的基金会)的发起人毛阿姨(毛爱珍女士)时,我才真正将自己所参与的事情以及方向定义为“公益”(也是在那一年遇到我现在的妻子),我开始筹划专职推动抑郁症等社心障碍群体的议题。
并于2012年底-2014年底的两年时间内,完成了“结婚”、“安家北京”的“现实基础”,于2014年底-2018年上半年的三年多时间里,出任尚善基金会项目总监、创办社会企业“阳光爱尚”、完成北京大学全日制首届社会公益管理硕士学业、创办民非“心晴心理”,用一句话总结:“如同走出抑郁症一般,我尝试了各种方法,一直坚持,却没有真正达成我想实现的目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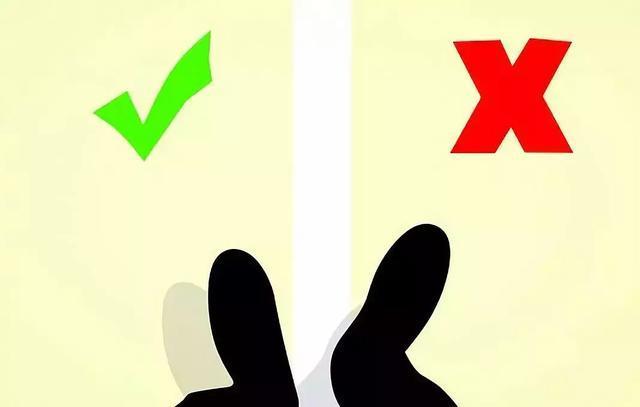
如果说2012年是一次转折点(那年我认识了胖子、对生活开始有了憧憬,那年我决心致力于抑郁症等社心障碍群体议题、投身公益),那么今年2018也是一次转折点:
1、我父亲过世了。父亲曾经辞职“陪读陪工”我8年,而我同样投入非常多的时间和精力陪伴父亲抗癌8年,父子情深;2、或许是父亲的过世,开启了我灵性层面的感知,精神层面的痛苦、障碍一下子通了,抑郁症、精神痛苦是一种“病”的体验,从不断减弱到一下子突然消失了;3、二十多年的“病患”经历以及十多年的群体互助经历,既让我有了丰富经验,同时也让我“彷徨”:当下社会上很多对抑郁症群体推动的议题未必是正确的导向;唯有“同伴支持”下的“自倡导”才是基本的尊重,才更有利于康复,才是我的方向。
只差一点点,今年我就从这个“圈子”退出了
不管是2012之前的“自娱自乐”,还是2012之后的“专职推动”,对我来讲都是一种“自救”。只不过前者是“疾病自救”,后者是一种“生命成长”,都是一种小我的动力。然而就在今年,父亲的离世给了我一次棒喝:我一下子就觉得自己“正常”了,所谓的“治疗”、“康复”依然是一种负性标签,跟我没什么关系了。
然而,看看我所在的“圈子”:圈内朋友都在急于“治疗”与“康复”,急于让大众“承认抑郁症等社心障碍是一种病,多加理解”;而社会大众在越来越多了解抑郁症等知识之后,对抑郁症等的防治依然不能有效提高认知,尤其是做不到真正意义上的尊重。

“小我”动力的减退,“大我”的某种无力感,我有些疲了:
1、“患者”及所在家庭,对问题通常“讳莫如深”,急功近利的关注如何治疗可以快速康复,却很少去自我倡导,其实带着所谓“问题”,我们一样可以热爱生活、提高生活质量、享受被尊重的权利,这样也更有助于康复。
2、社会机构层面(绝大多为草根),基本分为三类,最多的是科普传播,从医学层面告诉大家什么是抑郁症等精神疾患;其次是线上社群,多是抱团取暖、相互交流治疗方法;再次是线下活动,而线下更多也是抱团取暖和交流治疗方法。我几乎很少看到有推动“自我倡导”,很少看到有规模化、有体系化的同伴支持,而我的力量似乎也很难达到。
3、社区层面,在我所在的北京,我能看到政府为心障群体提供了活动交流空间以及相应的福利;然而就我了解的几个社区,参与度还不到20%(比如说一个社区有50个登记的患者,但能参与社区活动的不到10人),社区能给群体提供的服务内容也相当有限,更多是一种“短期托管”,难以解决真正问题和提升心障群体的幸福度。
4、社会层面,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随着越来越多抑郁症患者(尤其是一些名人)自杀事件的发生,大众尤其是生活在城市中的人们逐渐了解了抑郁症,然而这些了解更多却并非“尊重”与“同理心”,却更多是贴了“疾病”“自杀”“不正常”等标签,这与我们想推动的抑郁症认知传播并不相符。
5、医院层面更不必说,虽然越来越多的医生尤其是年轻医生认识到精神疾患的特殊性与复杂性,认识到医学对精神问题的局限性,但医疗体系的本质决定了:医院就是一个将精神问题视为疾病、视为异常的地方,与“同伴支持”以及“自我倡导”往往相悖。
我给妻子说:虽然我内心依然觉得抑郁症疗愈、精神健康是我的使命,但目前的环境实在无力下手,而且我自身问题已经解决,我们开启一种新的生活吧。处理完父亲的后事以及安排好母亲的生活,我找了新的工作(儿童教育领域,我天真的认为这样可以帮助很多儿童成长,也是一种预防)。
新途——突然敞开的新空间又将我拉回
新途是十年前创建于上海的一个社会组织,以服务于患者社群为主旨。我跟新途的发起人郭小牧老师在微信上认识是在2017年,本已约好在我去上海跑马拉松之际相见,后因父亲癌症的加剧我未能成行,再见已是今年7月份,那时我已经在新的教育公司里开始“试用期”了。
小牧老师跟我讲述了新途线下8个城市的社区体系以及新途未来要推的基于区块链技术的线上社群系统,我一下子心动了,并应约参与了新途在上海组织的一次工作坊。工作坊上我见到了自闭症、同性恋等“隔壁”社群的一些“领袖”,见到了新途的另一个发起人龙飞博士,两天的活动让我确认了新的希望:我并不想离开。
另一方面,我在具有较大规模的教育公司已经上班超过两周,一个最大的感受:这个公司的使命就是帮助儿童如何提高应试能力,如何去追赶社会的“成功”。这让我很失望,因为这不是我心目中教育的样子,这样的教育与促进儿童心理健康发展甚至相反。所以我决定:与新途一起,再试一把,万一实现了呢。
为什么要推动社群规模化?去中心化?数字化?如果用一句话回答:就是实现社群的价值,也就是实现“同伴支持”的价值。过去,人们常常争论是公益还是商业来解决这个群体的问题,这在我看来其实并不重要,公益还是商业,只是一种交易方式、由谁买单的问题,关键是价值的创造、规模与可量化。真正有了价值,而且可以计量,具备了规模,不管是市场还是社会,总会有买单方。
那如何实现价值创造?如何实现规模化?如何实现可计量?我参与和推动抑郁症社群已经15年了,从十多年前的BBS+QQ群+一些线下活动,到如今的微信公众号+新互联工具+微信群+一些线下活动,这个群体有发展,但并没有突破:
1、我们是封闭的,没有真正建立与大众的链接;2、我们是分散的,9000万抑郁症患者,更多还是一个个孤岛;3、我们是缺乏协作的,我们在努力告诉外界抑郁症的可怕,却没有将已有的自救模式和自我倡导有效联结。
我想说,包括我在内,很多推动社群发展和同伴支持的先驱是创造了很大价值的,很多同伴、家属、志愿者的参与也是创造了价值的,我们有疗愈作用的小组,专业人士的课程,康复者故事,同伴及家属的自我倡导分享,跑步疗愈活动,瑜伽疗愈活动等等……
但这些价值去哪了,我们自我倡导的效果又去哪了呢?我们创造的价值需要数字化可计量,才可以累积;通过去中心化,才可以实现规模化;通过规模化,才可以实现价值交易和可持续发展;通过可持续,才可以进一步促进价值创造与同伴协作,“同伴支持”与“自我倡导”才可以更有效推动。
我更关注“同伴支持”与“自倡导”的力量
刚过去不久的8月份,我去印尼巴厘岛参加了亚洲及亚太范围内关于“同伴支持”与“自倡导”的会议(这个组织的英文名是TCI,翻译过来是“跨亚洲心理社会残疾人战略小组”,机构的使命在此不再介绍,可以访问它们的中文网站:https://c.quk.cc/3/c2/xamsjgm32tx 北京大学首届社会公益管理硕士,马拉松爱好者,抑郁症、焦虑症、强迫症、恐惧症等众多心理疾病亲历者,走过了从严重心身障碍中康复并实现生命重建、回归阳光生活的艰难历程。曾坚持在抑郁症公益领域服务十余年,先后担任过心理健康类公益组织阳光工程总干事、北京尚善公益基金会项目总监和心晴心理健康服务中心理事长,现主导推动“抑路同行”精神健康关爱联盟。若您喜欢我们的文章,欢迎在文末打赏支持,打赏收入将全部用于内容生产上,为诸位提供更多精彩内容。
版权声明:文章为原作者授权发布,版权归原作者所有,未经允许禁止转载,如果有转载需求,请联系乐见岛运营人员。
“乐见岛”第四期乐平讲堂《解困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文化断层危机——儒家如何返本开新》正在报名中。
乐平讲堂是“乐见岛” 子栏目,每月我们都会邀请一名资深人士,探讨领域内关于创新解决方案的讲座。
本期我们有幸邀请到,著名国学大师赵士林先生为主讲嘉宾,为我们分享主题《解困21世纪中国的文化断层危机——儒家如何返本开新?》
所谓文化断层是指文化传统的断裂。这种断裂导致文化上的真空,导致个人在文化上的失根、失范尤其失去自信。没有了文化上的滋养,没有了千年传承的礼仪和教养,现代社会的公民文化又不可能一朝养成,人们不能不陷入困顿和迷茫,并被困顿和迷茫所焦虑。
马斯洛认为,人类的基本需要,即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需要的性质是类似本能的,一方面具有先天的、人种遗传的基础,一方面其表达又没有纯粹的本能那么强烈,而是脆弱的,还要取决于后天的学习等因素。
而越是高级的需要,例如自我实现,其本能的性质越弱,其表达越容易受环境的影响。也就是说,中国人要自我实现,必须要有一种强大的文化支撑。
中国人普遍人格的自信,与文化的自信息息相关。也就是说,中国人要普遍获得幸福感,必须弥补这个文化断层。
而儒家作为古代中国代表性的思想状态,今天如何评价和处理其思想资源,无疑是走出文化断层的困境,及中国转型进程不容回避的文化任务。
具体说来,如何看待对下一代的国学教育?又有哪些东西是在国学教育中值得我们注意的?如何通过国学减轻自己在工作生活中的焦虑感,迎来幸福美好生活?如何让国学于小处助己修身,在大处谋事帮人?我们期待一个答案。
适合人群:愿意思考的国人,尤其是在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上急于寻路而迷茫、并被迷茫所困扰所焦虑的年轻人;同时也适合商业的精英阶层;国学从业者及学习者;公益机构;等....























